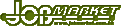雖然能到考評局門口來排隊的人不多,但徹夜未能入夢的師生該有不少吧?不知道此時此刻他們都在做些甚麼呢?趁機忘形狂歡以消憂解鬱嗎?沉醉在世界盃的興奮中瘋狂投注叫囂嗎?禱告靜修坐禪以求安心寧神嗎?有人像我這般為了壓抑紊亂的神經,鎮靜恍惚的心神而勉強集中精神重複打毛綫以圖換取短暫的專注嗎?
然而,一針一針地細數並沒有紓緩我過度緊繃的神經,排隊的人愈來愈多,打盹的人卻甚少。各自肚腸各懷心事,明明知道一切已經塵埃落定,心裏還是暗暗較勁。
「不早一點來不行啊,很快記者就會到學校門口守候拍照,遲了回去要挨罵呢!不是人人都能勝任這崗位啊,要知道要是出了甚麼亂子大家可怎麼敢擔當?」排在我們後幾個位置的工友姨姨自顧「吐苦水」,搭理的人都只有一句沒一句地嘻嘻陪笑虛應。是的,每人都有自己的崗位,走了岔路出了亂子,除了自己,誰又能擔當。我再次抽出放在文件夾裏預先備妥的文件,逐個逐個的在心裏背默早已熟記的資料,想起初春綿綿細雨的某天,自個兒在教員室的「街機」登入每個頑固、「甩漏」的學生的個人戶口,為他們列印繳費條碼,再「拉大隊」到便利店繳交留位費的時候,我們執着的早已不再是那一百五十塊或更早前分明知道是掉進鹹水海的四百三十元聯招報名費。
天微亮的時候,薄弱的日光像小心翼翼地推開緊閉一夜的窗簾,而未圓的月始終未願退席,長長的人龍早已拐彎又拐彎,站在氣味濃烈張狂不饒人的公廁外的人未見慍色,也許我多心,只覺隊列中那些深鎖的眉宇之間心事重重。我們這一群深宵陸續出動來排隊的人當中,情緒能夠比較抽離的大抵只有工友吧?為人師者多半略有牽掛,難怪來排隊的都是工友多,畢竟資料轉過幾手,應該是沒有那麼炙熱傷人的。然而,任誰來等待考評局開門,消費的都是精神消耗,有應屆考試班的老師來等待的話彷彿又是另一種煎熬,任教應屆考生的過度緊張敏感的班主任來守候更是有說不出的,使人神經衰弱的損耗。
(選輯自《怎捨得不做搣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