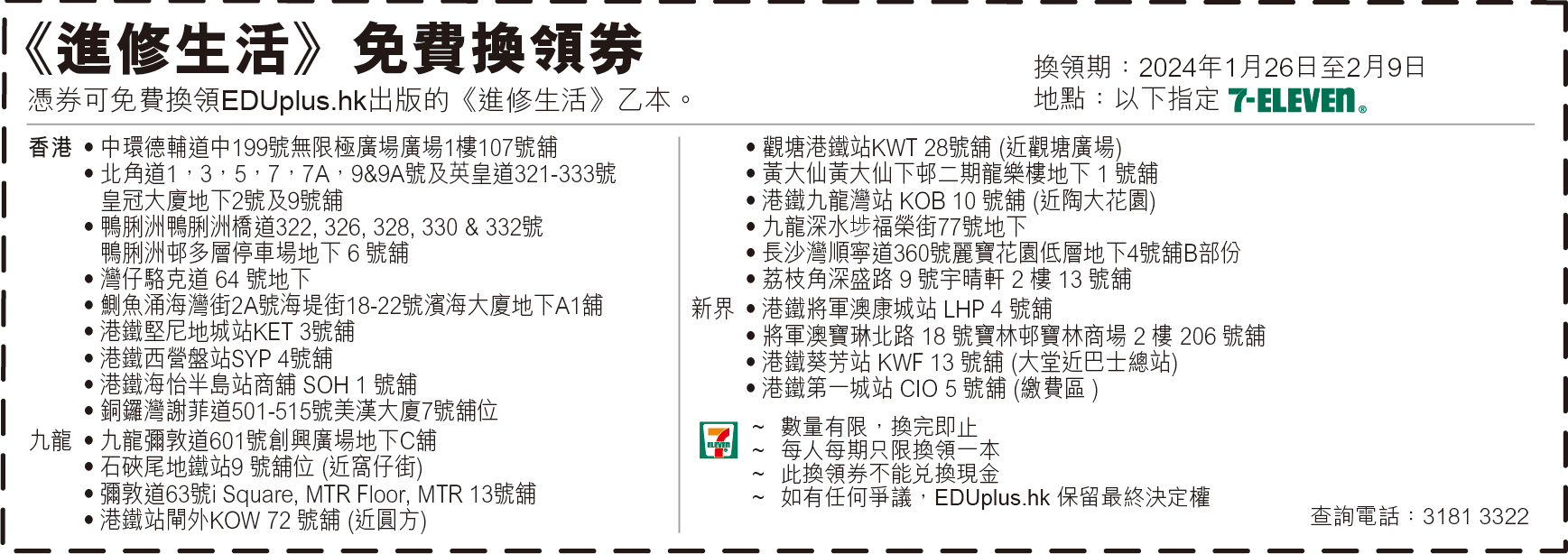記憶成為負累
Column
回顧2023年,恒生指數由二萬點下跌了百分之二十至約一萬六千多點,表現差強人意。在2022年底,新加坡的資產管理規模大約是三萬七千億美元,而香港是三萬九千億左右,相信到公布2023年底的數字時,新加坡已經彎道超車。可見地緣政治的影響力,而分析員之訓練主要以經濟學為主,再加上商業行為知識,可能對政治帶來的影響未能充分反映。
2023年初開關以來,我們以為會復常至2018、19年的景況,隨着時間過去,晚市不景氣、零售業不振興、旅遊業不似預期、自由行也不像往常一樣、股市成交量下跌、集資額暴跌、做生意的亦不好景,中層人才流失,加上財赤幅度加大,面向將來,道路仍然艱難。
筆者深感「復常」已不可以是香港的出路,如果我們只想像去做一些過往的事情,而去恢復過往的景象,我覺得失敗的機會很高。我們可能需要心態重新開機(reboot),把過去的都忘掉,不讓過去的情景佔據思維空間,騰出心力,去塑造一個全新的將來。記憶成為負累,蠶食了想像力。
但究竟有沒有人,或甚麼人可以提出一個願景呢?這要回到去市場主導還是政府主導的方針?如由市場主導,當中公司的高層要負責生死存亡,所以由高管提出願景,失敗了就負責任,公司最差情況是破產,同事可以轉職,家庭仍然存在,繼續生活,社會反而穩定,讓時間慢慢淘汰剩下的可持續業務。當中一定有新聞說某大公司破產,人們又去懷緬一番,說甚麼黃金時代過去了,但其實可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新企業的開始,不過新聞不會報道。
我有時會想,阿里巴巴的出現是否因為政府很想做電子商貿呢?當時最盛行的仍然是加工出口的製造業,但在無人歌頌的環境下,漸漸成就了一間跨國企業。香港70年代製造膠花、玩具、手表,做小販賣生果、豬腸粉,是否當時政府在分析完世界大局後,引領市民而得出來的繁榮呢?及後製造業北上,老一輩的工人失業,但他們的子女就透過苦讀變身專業人士,並投入服務業,當時出了不少醫生、會計師、建築師、測量師等等,養活自己的父母及下一代。如果只依賴一兩個主要趨勢去做事,人們便無時無刻想去配合,佔用了不少腦力,不利發揮其他想像的空間。但人類的心理就是討厭不確定性,如果沒有辦法知道做甚麼生意是最可持續,而有人(特別是政府)去提出,人們便會全力而去跟隨,萬一失敗了亦是一起失敗,但如果成功了卻沒有跟隨,就被排擠出外了,這叫後悔厭惡 (regret aversion),此現象在基金業經常出現,在大市上升時,明知太貴亦不甘沽貨;在大市跌時,明知太便宜亦不甘買入,因為如果自己是唯一一個做錯了的,年底的投資表現比同業差很多,可能連工作都失掉,不宜令自己後悔。別人做甚麼,我就跟大隊,只要在大隊中間,輸錢不是問題,賺少了亦不是問題?
回歸主題,香港的將來究竟是市場抑或政府主導呢?筆者知道政府可以摧毀市場,但市場的存在可以威脅但未至於可以摧毀政府,所以將來如何,還是「看官」吧!

AI仍然是2024年 科技預測的頂頭大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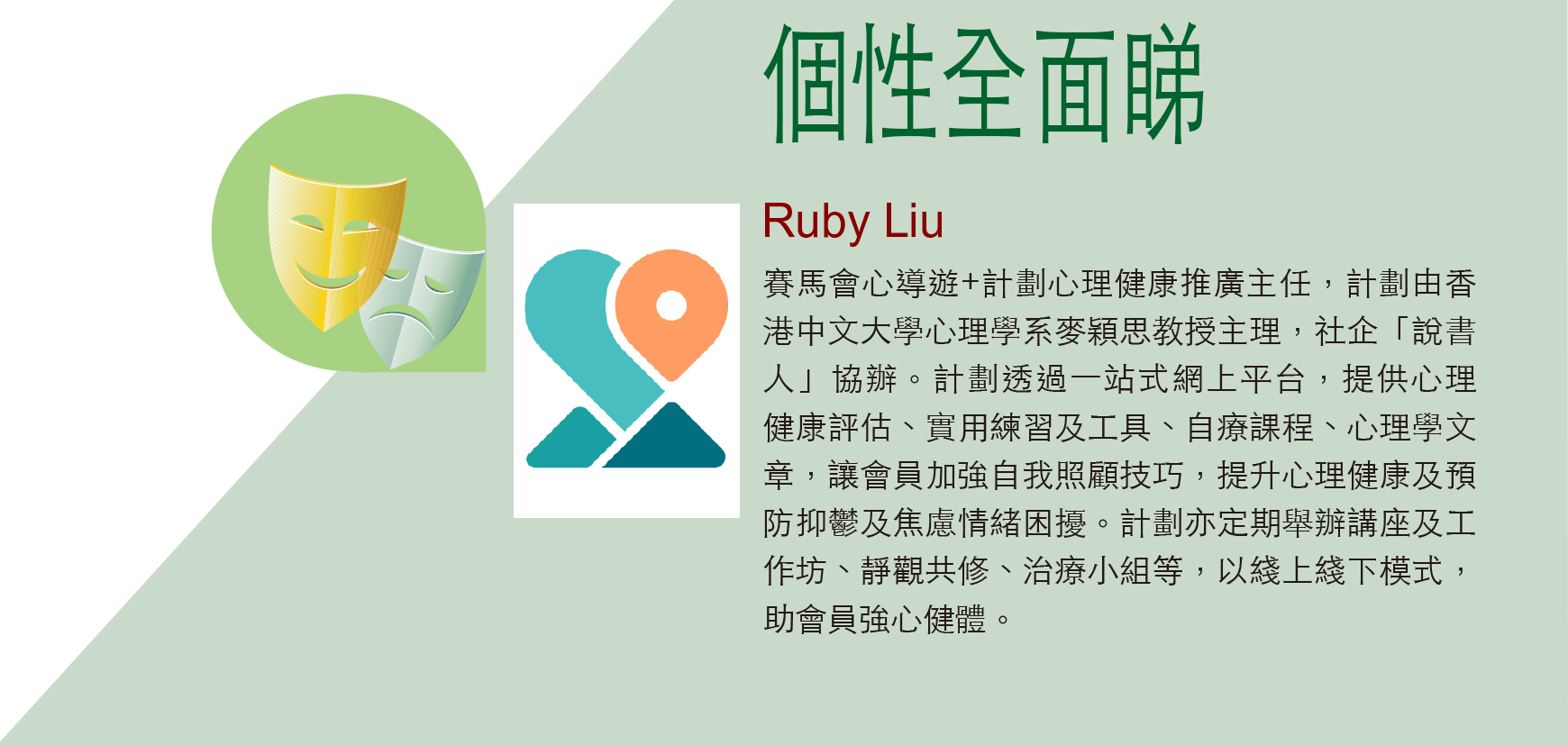
演算法的時間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