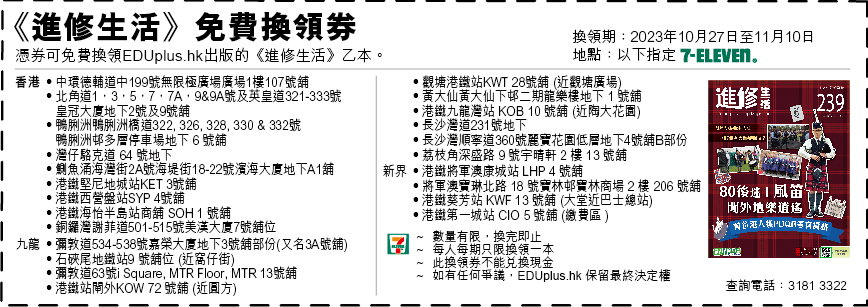不分膚色的界限 狄雷龍
People
全港只有二十一名少數族裔社工,印度裔的狄雷龍是其中之一,他同時是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多元種族社會工作分會召集人。生於香港,精通五種語言,包括流利廣東話,奈何因為天生的膚色,自小嘗盡被歧視和欺凌,他立志為自己、為族群帶來改變,半工讀奮發向上,好不容易實現當社工的夢想。
狄雷龍哼着Beyond的《光輝歲月》,「可否不分膚色的界限,願這土地裏不分你我高低」,道出心中理想,積極幫助少數族裔青年就業,全力為族群尋覓清潔和跟車送貨以外的工種。
狄雷龍流着印度族裔的血,但他和父母均在香港出生,住在鰂魚涌模範邨,家人日常講廣東話,開飯吃中菜,農曆新年也會派利是、吃蘿蔔糕。阿龍說:「我爸做工程,阿媽教書,他會講中、英語,不懂說印度語,阿媽更不懂做薄餅或印度菜。我去印度要申請旅遊簽證,當地人看我的衣着、聽我的口音,會認定我不是印度人。」
阿龍對香港很有歸屬感,但自小的遭遇卻令他常懷疑其香港人身分,初時以為問題出在語言溝通,但現實卻殘酷地告訴他,語言是其次,膚色是主因。「當年同邨的少數族裔青少年有二十多人,經常一起玩,大約十五歲,讀中三時,我們想加入西灣河一間通宵服務的青少年中心,享用中心的球場、遊戲機等,對方見我們一大班人進來,立即好驚,以為我們去搞事,不願意招待。」阿龍比同儕的廣東話流利,負責出面幾經爭取,他們才得以成為中心會員。
但阿龍仍不時察覺受到不公平對待,例如租場怎麼不是先到先得,而是某些人受到優待?他為這類事情去理論,後果是中心屢次報警。最後不歡而散,青少年中心將他們列入黑名單。就算阿龍現在是社工,仍然被拒諸門外,令他感到十分委屈。經此一役,阿龍決心要當社工,憑一己精通廣東話、英語、印度語、巴基斯坦語和尼泊爾語的本事,為多元種族居中協調,融入社會。
半工讀兩年 實現社工夢
阿龍家境不富裕,考上明愛專上學院社工高級文憑課程後,展開兩年的半工讀生涯,日間上課,夜間當保安員八小時,每周工作六天,月薪八千元,長期睡眠不足。這份保安工作薪金不多,但是得來不易,所以他堅持到底,「我應徵過十幾家管理公司,全部失敗,有僱主在通電話時答應聘用,但當見面時,馬上改變主意。更有僱主明言,他們管理的是高級住宅和甲級寫字樓,住客、租戶未必喜歡不是黃皮膚的管理員。」
在外面繞了一個大圈子,見識過後,他回歸少數族裔圈子求助,靠人介紹,才覓得通宵更保安工作,「曾經以為廣東話是少數族裔人士搵工的障礙,原來最大障礙是膚色。我是香港人,有『三粒星』,身分證是否需要加一欄註明膚色?」他感嘆:「時常有人說,少數族裔只信任自己的社群,遇困難時不向外求助,但事實是無論搵工或租樓,在族群裏互相幫忙是最快的途徑。」
同樣因為膚色,他經常在街上被截查身分證,甚至被帶返警署、被人問「印度人是否餐餐食咖喱?」、被流氓辱罵「死差仔」等經歷,阿龍說是家常便飯。他的爸爸為他取名「雷龍」,因為這是性格溫順的草食恐龍,但他間中也會沉不住氣,「我走入餐廳,店員第一時間當我是速遞員來取外賣。我有時會質問對方,為何不是跟我說『先生,幾多位?』或者『先生,買外賣?』,對方叫我別激動,我解釋,我激動,因我為受夠了!我希望店員得到教訓,學曉待客之道。」
中文和膚色 求職兩難關
三年前,阿龍學有所成,得償所願加入社工行列,成為全港二十一名少數族裔社工之一。他現在任職有提供少數族裔服務的社福機構,專責協助少數族裔青年找工作。勞工處向他們提供的職位空缺主要是清潔,阿龍也曾帶受助青年去大型招聘會求職,但面試後往往無下文,挫敗得多,他們不寄望這類流於門面的求職渠道。
廣東話和膚色依然是少數族裔兩大求職障礙,阿龍認為,有必要加倍游說僱主,「在現行教育系統下,無足夠資源讓少數族裔人士學好中文,雖然他們未必懂得寫中文,卻精通英語和本身族群的語言,例如印度語,完全勝任在電訊公司的客戶服務熱綫部門,專門接聽英語或印度語顧客的來電。香港寬頻僱用了他們,是增添一種語言優勢。」要物色更多這類僱主,談何容易,阿龍和同事們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仍然事倍功半,但阿龍說:「這三年,好開心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
少數族裔不論學歷高低,求職本身已困難重重,少數族裔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七,政府放寬輸入外勞的新政策令阿龍相當費解,「為何不聘用本地人?少數族裔家庭通常有六、七個仔女,較年長的仔女都會自覺有責任養家,好需要找到工作。」少數族裔釋囚的求職困難更大,阿龍正在進修,盼具備投考感化主任的資格,服務釋囚。
與華人共事 學相處之道
阿龍是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多元種族社會工作分會召集人,顧名思義,推廣多元種族共融,他期望政府的社會共融政策不是流於表面,除了資助社福機構服務少數族裔,更應該多從公眾教育做起,使華人與少數族裔互相認識,明白文化差異,了解多一點,誤會少一點。
阿龍本身也在適應職場文化差異,「自小接觸華人的機會不多,指定學校每級有五班,四班是少數族裔學生,一班是華裔學生,雙方不相往來,互當透明,不懂相處。現在的工作間只有我一人是少數族裔,是我第一次與華人共事。少數族裔大部分人習慣按指示辦事,但華人職場要求員工自動自覺,快手快腳,僱傭合約無寫的職責有時都要做,還有華人同事說話婉轉,我們未必明白當中含意,如果可以清楚說明就更好。」
阿龍嘗試找方法令自己日子過得舒服一點,他搬到中環,在不同國籍和膚色人士雲集的區域居住,「在這裏,我不是少數族裔,我得到別人尊重,開心好多。」他嚮往「不分膚色的界限」,但美麗新世界,仍需大家一起努力耕耘。
電視劇御用壞人
狄雷龍的爸爸叫狄龍,閒時會當特約演員,「電視台派給少數族裔人士的角色,往往是殺人犯、劫匪、強姦犯、難民、爛衫爛褲,形象不好。」兒子對此不以為然,爸爸卻享受演戲的樂趣。
「我自小看電視,望見我熟悉膚色的人,在戲劇裏都是壞人,感到十分可笑。沒有好人角色可以演嗎?創作自由之餘,應該要有平衡。電視觀眾多,每個畫面都在教育公眾,如果少數族裔永遠飾演壞人,社會對我們的印象會變成怎樣?」狄雷龍認為,潛移默化的力量,絕對不容忽視。